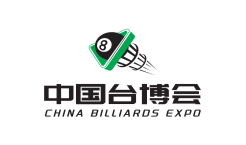原文: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湖心亭看雪》全篇159字,文笔简洁凝练,但无论是叙述还是写景,都自出心裁,生动传神,读来让人明其事,见其景。更妙的是,作为回忆主体的作者并未即事发一言,抒一情,但读者似乎已能想见张岱对湖心亭雪景的喜爱。这是一种不大声呼号,而是如“弦弦掩抑声声思”般欲遮还羞的情感。
这不禁让人困惑,借事说理、借景抒情难道不是绝佳的创作手法吗?看来,我们只有了解张岱写此篇时的创作背景,才能明白他“似述平生不得志”的写作心理。
正如张岱众多记昔游之作一样,文章开篇“崇祯五年十二月”,作者采用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国已灭,家何以在?就是这样一个无家无国之人,也许,在某个无眠的雪夜,他想是否可以像东晋王子猷“雪夜访戴” 那样趁兴夜游,可他又该去往哪里?就算他愿意舟车前往,此时的西湖还是当年的西湖吗?
作者望夜兴叹,提笔缓书,追忆那一次“湖心亭看雪”。
那年西湖大雪,三日未霁,“人鸟声俱绝”,想这样清绝之地定是在待有缘人而来。他在悄悄等待合适的时机,于是,“是日更定矣”,张岱雪夜独往湖心亭。
大雪覆盖下的湖心亭,已是极寒之地,舟行之时,只见天云相溶,山水一色。如此,孤怀雅兴之人,竟也能如陶公那般自谕:此中有真意。真意在哪?真意就在那湖上影子,一痕长堤,一抹湖心,一芥孤舟,以及舟中两三人中。此时,张岱大概慢慢明白,所谓家破国亡之感,不过是那亘古浩渺沧波中的一种随波逐流,又或是那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改头换面。流波也好,头面也罢,终是会被大自然的风雪覆盖的。
走到亭上,竟早已有两人在此“铺毡对坐”,他们见张岱孤身一人,拉其同饮。被两人的热情所感染,张岱决定痛饮一番。酒酣兴尽之后,张岱问起两人姓氏,两人避而不答。张岱猜想既是一面之缘,酒水之交,又何必知道对方的姓氏家族呢?怕张岱有所介怀,对方解释说:“你既于深夜在此遇见我二人,定知我二人非追名逐利之人,既非名门望族,不提也罢,我们不过是客居在此的金陵人。”
张岱听罢,心下默然:自己和他们又何尝不一样?
告别二人,再乘船回去,夜色更深了,湖中风光已不再是张岱所关心的,因为亭中两人已给了他想要的答案:天地万物变幻易逝,国恨家仇也可以随风遣散,乱世下的士人,怕只怕知己难逢。
等到下船,一路陪同的船夫喃喃说道:“ 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张岱自笑道: “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他明白,踏上归途之后,心里期许的是,下一次“湖心亭看雪” 会遇到下一个“自己”。
谁知,这一别,便再也没有了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