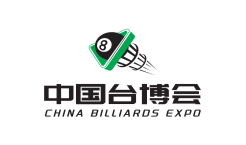杰克与艾伦
如果60多年之后,一个杰克·凯鲁亚克和一个艾伦·金斯堡再度相遇,他们还能一见如故吗?
我相信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反对派团体像今天一样多样,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民权倡导者、女权主义者、男女同性恋者以及波希米亚人之类,五花八门,然而,在意识形态上,每个团体并不是那么僵硬的,不像今天,动不动就与其他群体争吵,或者把内部的不服从分子踢出群。他们都清楚,他们共同的大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个体、对文化的压抑。没有什么比反对这个敌人、谋求个性释放更大的共同诉求了。
凯鲁亚克如果活在60多年后,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和金斯堡根本就势不两立:金斯堡是个学院派,理论高人,出入于赫赫有名的“纽约知识分子”圈子,以犀利地批评美国为毕生的志业;而他自己则是个爱国者,看到美国国旗冉冉上升时都会掉眼泪。他们两个早在二战末就见面并互通书信了,金斯堡在一封信里说,凯鲁亚克有一个“外邦人的大脑”——“goyishe kopf”,意为“不开化的笨蛋”。这词有着《圣经》渊源,是金斯堡针对凯鲁亚克念念不忘自己的宗教背景所作的讽刺,凯鲁亚克用一种颇悲伤的口气回信反诘说,他一向跟金斯堡那个圈子的人,那整个的“知识分子气氛”是对立的,他的人生的早年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敌对中度过。这种气氛自发地排斥他:
“因而引起了我无数的懊恼,以及憎厌……我整个清醒的本性告诉我,这类事情于我而言是道不同的……我是耶和华的儿子——我战战兢兢地走向那些眉头皱拢着的长老,他们好像知道我的每一个过失,并且准备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惩罚我。”
凯鲁亚克的回话引来了金斯堡更锐利的分析。他复信说:“你感到的‘懊恼’是公然的外部化(avowedly exteriorized),你害怕……在外部意识到你那致命的缺陷。”
两个人的话都不无晦涩。凯鲁亚克从来乐于自比耶稣,讥讽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手的文化贵人不知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福音;金斯堡则指出他自称懊恼,是把压力和责任推给别人,而不敢跳出自身来看到自身的问题。当1957年,维京出版社将《在路上》推向市场时,我们在书中依然能看到凯鲁亚克对纽约的理论家们不留情面的挖苦:“我的纽约朋友们,所有人,都待在一个噩梦一样的消极的位置上,他们都在贬低社会,利用他们迂腐乏味的文学、政治或精神分析方面的借口。”与之相反的是他的朋友迪安·莫里亚蒂,他只是“在社会上奔跑,渴念面包与爱情”。
但书信中的冲突,不妨碍两人是实体世界里的好友。最新中译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人:金斯堡文学讲稿》中,身为同性恋者的金斯堡,把他们的初识写得如同一见钟情,你可能必须克服乍看之下的不适,去熟悉这些人身上的好处。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大一下半学期时,金斯堡经好友吕西安·卡尔的介绍去见凯鲁亚克。“凯鲁亚克是一个非常成熟、敏锐、善于观察、宽容的人,我们双方都怀着好奇心。他看到了我的浅薄,我也看到了他的野性。我爱上了吕西安,我也爱上了凯鲁亚克。”这场交往的结果,是“我发现我可以同时爱上很多人”——这是多么美好的发现。
炫与酷
凯鲁亚克这位率先定义了“垮掉一代”的作家(他有一本书就叫《垮掉一代》),自己也成了“垮掉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很不寻常。一般人或许就简单地理解为凯鲁亚克太想成名了——他想自任旗手,成为文学界瞩目的明星和年轻人的偶像。然而,根据给他写传记的安·恰特斯的记述,《在路上》出版之前,凯鲁亚克就不无难过地告诉朋友们,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中产阶级青年的时尚”了,那意味着他将变成符号,被社会中追求体面和稳定的那一部分人据为己有,他的浪荡不羁的宣言将补足中产阶级的个人形象里比较缺少的那部分内容。他的预见是对的,更加难堪的是,他必须去应付随之而来的出版宣传活动,这着实不是他想要参与的事情。
他被名声所折磨,是有很多证据的。从他留下的众多肖像照里,我们几乎看不见一个稍许志得意满的凯鲁亚克,他总是有种凝重的神色,即便是早年,套着一件橄榄球服、显出傲人的身材时,他的表情也不是得意的,而显得有心事。酗酒——可以称之为“不自重”的表现——是为了纾解压力,违背他本意的名声,对他则是一种重负。他拿着赚到的版税搬回到他那位虔信天主教的妈妈家里:他从未想过与那个落后的世界断绝关系。
所以凯鲁亚克值得认真对待,我们要看到,他即便不排斥成名,也绝不肯背负”呼吁幻灭的年轻一代一道堕落”的名声。根据金斯堡的解释,Beat Generation一词源于凯鲁亚克和约翰·克列侬·霍尔姆斯的一次闲谈,凯鲁亚克用它来概括他那一代人。霍尔姆斯在1952年写文章推出了这个概念,而当媒体开始大肆采用它时,凯鲁亚克立刻予以解释说,BG并不是“完蛋的一代”“毁掉的一代”的意思,Beat含有卑微和谦逊的姿态,此外,Beat在英文中还有鼓点的意思。最后,Beat被释义为Beatific,即“安详”,以及Beatitude——“八福”,这都是基督教的概念。
这样的澄清,一直是需要的,谁能体会到《在路上》的作者心里牢牢地存有“八福”呢?
而他因提出并代言了“垮掉一代”运动而受到的抵制,自始就非常激烈。年长一些的人,一般就把他看成是常见的反叛父辈的青年,名噪一时而已,而同样标榜“愤怒”的人,像同期英国“愤怒青年”运动的几位干将如约翰·韦恩等,又会觉得美国人都不严肃,都是奔着颓废狂乱而去,自己才是有着社会担当的。对此,凯鲁亚克在《“垮掉一代”之缘起》中,对自己进行了捍卫:
“不,我愿为事物代言。为了十字架说句话,为了以色列之星说句话,为了一位史上最神圣的德国人(巴赫)说句话,为了亲切的穆罕默德说句话,为了佛陀说句话,为了老子和庄子说句话,为了铃木大拙说句话……为什么我应该攻击我生命中热爱的事物?这是‘垮掉’。就这样生活?不,爱你的生活。”
这是很有特色的语言,称得上“炫”(hot),与之相对的,如他本人所说,是嬉皮士式的“酷”(cool)。嬉皮士和垮掉派在20世纪40~50年代之交几乎同时登上美国亚文化的舞台,“炫”不像“酷”那样故意偏离正规和体面,“炫”似乎主要是一种欣赏型的姿态,欣赏自己也欣赏他人,称赞历史上精湛而独创的思想,但不会悲天悯人(凯鲁亚克对政治的确不感兴趣),更多的是在孤芳自赏之余,记录下与伙伴们的同游同在。他说“喜欢”的时候远多于说“恨”的时候;他甚至讲,那些看起来活像罪犯的嬉皮士,他们“总是念叨的事情也是我喜欢的事情”,而嬉皮士运动也一向视他那一伙为同路人。
萨尔还是迪恩?
他旺盛的写作生涯持续了十年左右,写出的不少作品都直接表现“垮掉派”日常,如《达摩流浪者》《孤独旅者》之类。“垮掉派”的伙伴感非常强,《达摩流浪者》中讲述的禅修派对、结伴旅行,夹杂着各种酒精作用下的粗话和对性事的恣情谈论,但发自肺腑的讨论更是无处不在。虽然凯鲁亚克一向对诸如“禅”“精神分析”之类理论化的东西不感兴趣,但书中那些讨论禅修目的,讨论该上怎样的地方去体会更加深刻的禅意,讨论在旅途的下一站会有怎样的际遇的人,得到的都是正面的描绘。他们完全不为改变世界操心,而只在意自己善意的追求。书中的贾菲就对雷蒙说过:
“你和我都不是那种愿意为了过优裕的生活而践踏别人的人。我们的理想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永远为所有的有情祷告。”
金斯堡不愧是纽约大批评家莱昂诺尔·特里林的得意门生,他准确地把《在路上》的风格定为“自然旋律主义”。书中的尼尔·卡萨帝着实迷人,整篇作品里,他用各种小小的作奸犯科为这一场公路旅行,同时也为记录这场旅行的散文提供持续的动力,持续地为其加速。他们在用这速度纪念他们的时光,同时也在纪念他们所经过的地方、看到的事物、谈及的话题。在行动速度已越来越不成问题的当今,读《在路上》依然是一场感觉被它“带节奏”的体验,只是大量喝咖啡和通宵达旦服用安非他命的情节才会让人冷静下来,知道此事不可效仿,犹如不可效仿《水浒传》里那些行动坐卧动辄安排上三碗大酒的好汉。
正像凯鲁亚克的气质所显现的,他是个总有心事的人。金斯堡当年讽刺他,就是直指他的心病:他为没能继承父母留下的传统价值观而内疚,同时,他又不自觉地对波希米亚式的地下社会怀有迷恋。《在路上》中的这一群伙伴里,萨尔·帕拉迪斯从未停止一种幽怨:他埋怨自己因为抑制不住的爱而跟随了迪恩,从而离开了社会的正轨,尽管他们一道度过了诸多难忘的日夜。可是人们都想当然地把凯鲁亚克等同于迪恩·莫里亚蒂,而非内心矛盾的萨尔。
《在路上》出版于1957年,之后,凯鲁亚克曾写信联系马龙·白兰度,请他买下电影版权,并饰演迪恩,而他自己出演萨尔。他在信中设想好了拍摄技巧:在汽车前座上架起摄像机,日夜拍摄从道路延伸到路边风景的美妙镜头。他还说,拍电影,给自己的银行账户充入一条持续的现金流,是为了扶助他心爱的妈妈,并承担他接下来要去日本、印度、法国等地的旅行开支,此外他还说,美国的电影和戏剧都让他失望了,他想要来一番“重做”。
这野心可谓不小,可对当时如此有名的他来说,却也是一番绝望的努力。马龙·白兰度并没有理会他,恐怕也不理解他想要把自己和萨尔·帕拉迪斯合为一体的强烈愿望。作为垮掉派运动的灵魂人物,凯鲁亚克对于真实地表达自己并准确地被人领会这一点有着过于强烈的执念,他并没有考虑如何更妥当地利用好自己的走红。
来来回回地开车
青年学生是凯鲁亚克追随者中的主力,逼近20世纪60年代时,他们的群体在垮掉派等亚文化运动的感召之下,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批判性的反美态度,这跟凯鲁亚克的秉性完全不相容。他退出了垮掉运动的第一线,回到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母亲的家中,也不再写什么能让人记住的东西。金斯堡却一直活跃着,他所做的一件事,是为杰克·凯鲁亚克开创的事业辩护,为他的天才和人格辩护。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金斯堡经常提到诺曼·波德霍雷茨的名字。犹太人波德霍雷茨当年是一位批评界新锐,他在《在路上》出版后连续写出多篇文章,批判“垮掉派”不是什么文学救世主,他们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病症之一,而不是对病症的治疗手段。他的一篇发表在《党派评论》上的文章《一无所知的波希米亚人》,完全否定了金斯堡、凯鲁亚克等人的成就,他说他们写的故事很差、诗很差,本身也是坏人,他们怂恿人产生危险的冲动。他说,“垮掉派”和那些穿皮夹克、腰佩弹簧刀的青年飞车党没什么两样。
“即使是凯鲁亚克书中相对温和的精神,也很容易溢出来成为暴行,因为这些书中有一种压抑的呼声:杀掉那些能发表连贯的言辞的知识分子,杀掉那些安安静静地一连坐上5分钟的人,杀掉那些无法理解的人——那些能认认真真地和一个女人、一份工作、一项事业打交道的人。”
波德霍雷茨身上有着高级知识分子的洁癖,天然地不信任“垮掉派”那种趋于自动化的、在他看来不讲究美感和文字精确度的写作。谁知金斯堡是如此认真的人,他请波德霍雷茨来跟凯鲁亚克和他自己见面,见面是人和人交往的正途,居于文辞是非之上。那是1958年秋的一个晚上,他们三人碰面了,波德霍雷茨后来回忆说,金斯堡用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反复地说服他去领会凯鲁亚克的才华,而贬低他那自以为是的“有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波德霍雷茨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他发现他和金斯堡处处都是相反的:在同性恋的问题上,在对家庭的看法上,在对美国中产阶级总体情况的判断上……
其实他们双方都对对方的世界有所向往:金斯堡本来就出身纽约知识分子圈,却加入了“垮掉派”,他以1955年的《嚎叫》“出圈”,几乎宣告了自断回归那个圈子的路,只能去拥抱“垮掉派”许诺的那种追求更大强度、更大自由的生活方式;波德霍雷茨也未尝不对稳定的日子心生遗憾,他也是个年轻人,也好奇自由上路的感觉,也渴望性冒险,也会感到在婚姻家庭的问题上受了长辈的欺骗。
但他们终究是谁都没能说服谁。在这本讲稿里,金斯堡显示了他的气度:这个以“嚎叫”发家的文化名人几乎没有对任何批评者有报复的言论,也没有用什么不入流的笔法去揭发别人,更不曾掰扯自己那个圈子的人的私事。对好友凯鲁亚克,他除了赞许外就是惋惜,他惋惜凯鲁亚克在《在路上》之后的消沉,没能再出产更好的作品,通过描写他的好友如何忠实于自己完全私人的反叛(是时势违背他的本意,将它“扩大化”为一场亚文化运动),他也对凯鲁亚克尽到了忠实。
凯鲁亚克去世后,另一位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的“垮掉派”成员加里·斯奈德,曾于1969年发表演讲。他选定的精神归宿是“荒野”——美国在这方面条件得天独厚——他凭此对“垮掉派”的“在路上主义”提出批评:“你本该做的是走进野外的空间,过了100年后,你最终做的是来来回回地开车,能开多快就开多快。”在斯奈德看来,凯鲁亚克们是一些无路可走、只好绕圈子的假牛仔,他们离不开城市,离不开汽油,并不需要真正的大自然。这批评也是对的,但悖论的是,假如不从曼哈顿的地下社会发起,不依赖出版、派对和伙伴关系的蓬勃表达,“垮掉一代”又如何成为足以影响历史、感召后人的文化事件呢?